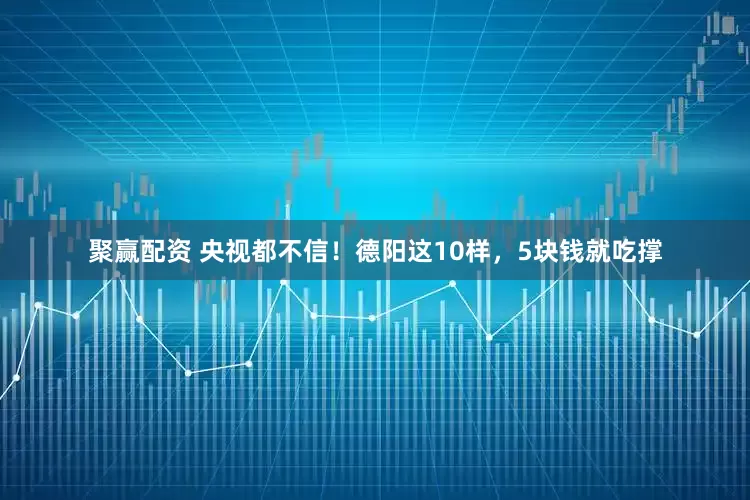
央视都不信!德阳这10样,5块钱就吃撑
图片
德阳的吃食,藏着老辈人的讲究。
三星堆挖出来的三足陶锅,看着就像现在火锅的祖宗,
四千年前,古蜀人围着它煮肉,花椒的麻早就在那会儿扎了根。
李调元这人有意思,在《醒园录》里说做菜得讲中和,
把宫里的法子和乡下的道道揉一块儿,德阳街头就有了那股又香又辣的味儿。
他在罗江弄的豆鸡,腐皮裹着香菌,素的吃着比肉还香,成都花会都给了好名声。
图片
广汉缠丝兔,那麻绳缠了三百年。
嘉庆年间,老乡用十几种香料腌兔肉,麻线从脖子缠到腿,挂在房檐下,风一吹,香味能飘半条街。
代木儿在连山供销社做回锅肉,肉片大得像巴掌,在油锅里滚成灯盏窝,香味能勾得人直咽口水。
本来是穷人家解馋的,就因他认死理,连山镇成了回锅肉之乡,桃花开时,好多人坐拖拉机来吃。
图片
移民来的人多了,德阳的饭桌也热闹起来。
北方的酱肉、江南的糖,跟本地花椒一混,啥味儿都能融到一块儿。
孝泉镇回民做的果汁牛肉,外酥里嫩;
中江人压的面条,薄得能透亮。
这些手艺在祠堂里传着,过节摆九大碗,白果炖鸡混着咸烧白的香,老人说这是吃福,年轻人直播给外头的人看。
现在厂里能大批做火锅料,可小店里还守着老法子炒底料。
三星堆的陶锅进了博物馆,可那股热辣劲儿,还在德阳人骨子里。
这儿的吃食,既有李调元说的雅致,又有乡下的豪爽,就像那回锅肉的辣,吃得痛快,还让人记挂。
图片
中江八宝油糕
这名字听着就透着股富贵气——清朝那会儿,它可是中江大户人家茶桌上的稀罕物。
《中江县志》里记着,乾隆年间这糕点就端上了达官贵人的宴席,八样宝贝料凑一块,金贵得很。
如今倒好,街头老灶台一摆,咱普通百姓也能咬着皇家同款,你说这日子过得,美不美?
做这糕的讲究,跟绣花似的。
鸡蛋得挑土鸡下的,打进木桶里还得用手把蛋黄挤烂,掺上川白糖、花生油、面粉、蜂蜜、玫瑰泥,揉得跟绸子一样顺滑。
装盒更有门道,梅花形的铜模子里先抹层菜籽油,倒上拌好的料,撒把碎桃仁、蜜瓜片,中间还得搁颗蜜樱桃,活脱脱一朵金边梅花。
烘烤时底火比盖火旺些,烤得糕体鼓起来,表面泛起谷黄色,那香味能飘半条街。
咬一口试试?
外皮酥得掉渣,里头软得像咬着云朵,蜜瓜的甜、桃仁的香、玫瑰的鲜全在嘴里打转。
老中江人会说:“这味道,硬是安逸惨老!”甜而不腻,油而不齁,连牙口不好的老人都能抿化。
图片
什邡米粉
汤头一端上来,那股子酸香直往人鼻子里钻,像极了老辈子说的“岚哟得很”。
这碗粉的渊源要追溯到光绪年间,城北鼓楼街的周永兴最初摆摊卖合脂粉,
后来琢磨出用本地大米发酵的绝活儿,
生浆粉劲道得能弹牙,熟浆粉软糯得化在嘴里,全凭那瓮子里捂足半个月的酸浆。
米粉店遍布街巷,老什邡人清晨五点半就揣着搪瓷缸缸来排队,
喊一声“二两熟浆,牛肉清红”,师傅抄起竹篾网就把粉烫得恰到好处。
红油汤底飘着白芝麻,清汤里浮着葱花,夹一筷子粉裹满肉臊子,再嘬口骨汤,浑身毛孔都张开了,比涮坛子还解馋。
外地人总问为啥啥邡粉这么“响呱呱”,
老食客眯眼笑:“你尝口发酵的酸香就懂了,这味道捂在米浆里,跟啥邡人的日子一样,越陈越有滋味。”
图片
罗江豆鸡
这物件儿,打清末光绪年间就飘着香了。
袁通儒老爷子在罗汉寺当和尚那会儿,把各家佛门的素食手艺摸了个透,还俗后拿房东送的豆皮捣鼓,硬是把这素鸡做出了肉滋味。
你说怪不怪?
豆浆面上那层薄皮,拿竹签儿挑起来晾干,裹上芝麻、花椒、酱油,蒸得透透的,
咬一口“巴适得板”,咸香里带着麻,软乎又化渣,跟真鸡胸肉似的。
老辈子说,1936年成都花会上,这素鸡一摆出来,和尚老道都抢着尝,直接得了“罗江豆鸡”的金字招牌。
现在工艺更讲究了,黄豆要泡足十二个钟头,磨浆、滤渣、熬皮,每道工序都马虎不得。
你瞅那金黄的豆卷,裹着秘制调料,蒸得油亮亮的,光闻着就流哈喇子。
德阳人摆龙门阵总说:“这豆鸡硬是安逸,比肉还香!”外地人来了,不揣两包走都算白跑。
图片
广汉金丝面
这碗细得能穿针的“神面”,可是广汉人百年来的骄傲。
说起它的来头,要追溯到1912年,广汉城西的高家面店。
老高家不用一滴水,全靠鸡蛋和面,再用竹杠压、大刀切,硬是整出了这细如发丝的金丝面。
你晓不晓得?这面细到啥程度?
最细的地方只有0.067毫米,比头发丝还细,真的能穿针!
2023年,这手艺还成了省级非遗,算是给咱广汉人长脸了。
这面吃起来,那叫一个巴适!
面条滑溜溜的,像小溪水一样钻进喉咙,蛋香混着面香在嘴里打转。
汤头清亮得很,用老母鸡和棒骨熬了四五个小时,
再撒点葱花、滴两滴红油,那叫一个安逸!
广汉人早上来一碗,精神一整天,比喝咖啡还管用。
现在到三星堆耍,哪个不切尝一碗?
图片
玻璃抄手
那可是老饕们心头的一颗明晃晃的“宝器”。
这抄手皮薄得透光,像玻璃片儿似的,里头馅料看得清清楚楚,所以得了这个名儿。
早年间,广汉人靠这手艺在街头支起摊子,清汤红汤各有一番天地,清汤鲜得眉毛都要飞起来,红汤麻得人舌尖打颤颤,巴适得板!
要说这抄手的皮子,可是个技术活。
面粉里掺蛋清、撒盐巴,揉得软和和的,再醒上两回,擀面杖来回压,最后薄得能透字,跟蝉翼似的。
馅料也讲究,荠菜切得碎碎的,混着火腿丁和肉馅,鲜香直往鼻子里钻。
煮的时候火候要准,水开了下锅,点两回凉水,皮子半透明,馅心刚断生,这会儿吃最是嫩气。
广汉人吃抄手爱配句方言:“这抄手,安逸得喊!”
红汤里头浮着层红油,撒把葱花,香得人吞口水;
清汤则用骨汤打底,鲜得眉毛都要掉进碗里。
要是冬天来一碗,热乎气儿直往心窝里钻,浑身都暖洋洋的。
图片
什邡荞面
光绪年间永兴镇杨家祖辈琢磨出来的压榨工艺,原本是当药膳给病人吃的。
荞麦面掺点白面,压成细丝,再拿竹匾摊开晒,白天晒得脆生生,夜里静置吸露水,
这“阴阳调和”的法子,跟马祖禅道的“道法自然”一个理儿。
这荞面颜色发灰,煮出来却透亮,夹一筷子“吸溜”入口,麻、辣、酸、烫四味在舌尖打转,
比普通面条多股子野性。
最绝的是那股子荞麦香,像山风裹着青草味往鼻子里钻。
老辈人说,当年走马祖寺烧香的香客,都要揣把干荞面当干粮,说“吃口荞面,心就静了”。
图片
德阳粉子醪糟
这碗软糯香甜的“岚哟”,藏着巴蜀大地的烟火气。
传说唐明皇为哄杨贵妃,在骊山修宫时,民夫剩饭发酵成醪糟,自此这口甜润便在蜀地扎了根。
德阳人做醪糟讲究“手挼”,糯米粉子揪成不规则小坨,
丢进红糖醪糟汤里煮得浮起,打个蛋花撒把枸杞,热乎乎端上来,那叫一个“巴适”!
粉子入口弹牙不粘牙,醪糟汤甜中带酒香,冬日喝一碗浑身暖,夏日冰镇着吃更解暑。
老德阳人讲究“自家曲子自家米”,酒曲里掺着草药,发酵出的醪糟酸甜平衡,比买的更“安逸”。
街头老摊子常说:“这碗粉子,煮的是光阴,喝的是人情。”
图片
红白豆腐干
民国那会儿,山里人用石磨磨豆浆,拿漆树叶子消泡,
五倍子花汁当卤水,做出的豆腐灰黑如墨,却成了蓥华山香客的“白牛滚水”,
嫩豆腐蘸盐辣子,配两盅山酿,解乏又顶饿。
后来尼姑庵的秘方传入,五香卤汁一浸,干香麻辣,成了佐酒的“硬通货”。
这豆腐干四角方正,表皮深褐如枣,里头却白得像羊脂玉。
咬一口,紧实有嚼劲,五香味里混着汉源花椒的麻、20味香料的醇,后劲还带点山泉的甜。
老饕们都说:“这味儿,比羊肉还暖胃!”当地人管好吃叫“岚哟”,
这豆腐干确实当得起——麻辣的“巴适得板”,本味的“涮坛子”清淡,咋吃都香。
图片
德阳片粉
这事儿要追溯到光绪年间。
梓潼东坝的仇师傅用绿豆粉兑菠菜汁,拿铜锅在沸水里荡出张张绿膜,冷却后切成两指宽的条,这手艺在旌湖边传了四代人。
片粉滑得跟德阳旌湖的春水似的,夹起来颤巍巍的透光。
老饕们都知道要"三拌":先淋红油让每根粉条裹上琥珀色,再撒花生碎增香,最后点两滴保宁醋激出酸味。
夏天来碗绿的,冬天要碗白的,调料台上的蒜水、花椒面、大头菜颗颗摆得齐整,跟化学实验室的试剂瓶似的。
"老板,多加点海椒!"文庙广场的夜市里,这样的吆喝声能飘半条街。
片粉摊子前头永远围着一圈人,塑料凳上坐的尽是端着不锈钢碗的食客。
图片
嚼雪包子
白面皮子裹着精瘦猪肉馅,蒸出来雪白松软,
像刚落的头场雪,咬一口肉汁直冒,巴适得板!
这包子皮有讲究,五斤白面掺半斤老面,加饴糖苏打发得暄腾腾。
馅心更实在,五斤肉剁得细碎,炒得喷香,掺玉兰片、金钩、醪糟,咸鲜里带点回甜。
老德阳人早上端碗稀饭,夹个嚼雪包子,岚哟,那叫一个滋润!
如今虽演变成小笼汤包,但老味道还在。
蒸笼一揭,热气裹着肉香扑面来,响呱呱的食客们挤成一团,生怕抢不着头锅。
这嚼雪包子,吃的不仅是味道,更是德阳人骨子里的实在劲儿。
图片
灶上的烟散了,碗底的红油凝了,人还坐着。
德阳的吃食啊,说到底,是吃个'人味儿’。
甭管三星堆的陶锅搁博物馆多金贵,厂里的料包卖得多远,
您瞅——街角那家,老板还守着油锅等灯盏窝呢。
日子啊,就在这热辣辣的碗里泡着,烫嘴,可您舍得放下?
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,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,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,请点击举报。鼎盛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